随着我们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完成认知任务,当我们将认知活动外包给人工智能时,我们的大脑使用量会减少,我们是否需要担心大脑退化得更快?
我得承认,这大概率会导致认知能力下降。
技术导致某些旧技能衰退,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
毛笔被钢笔取代,人们口算心算能力因计算器的普及而下降,
手写技能因键盘输入而退化,
自打我开始使用笔记本电脑,用笔书写的几率就大幅度下降,并且也越来越依赖敲击键盘,似乎指尖在键盘上敲击的过程更能促进大脑机车的运转一样。
于是乎,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的手写能力在快速下降,到现在,连“焦建利”三个字都越写越丑。
所有这些,都可以视为是技术导致旧技能退化的鲜活例证。
然而,如果我们将这一过程简单地概括为“技能退化”,那可能就忽略了其复杂性和多面性。
无数历史事实告诉我们,技术与技能的关系更像是一场持续的转化与重构(transformation and restructuring),而绝非单向的线性衰退。
1、技术背景下的技能的替代与新生:
每一次技术革命,在淘汰旧技能的同时,几乎都催生了对新技能的需求。
例如,工业革命虽然让许多手工艺人的精湛技艺变得多余,但也创造了机械制造师、操作和维修机器的机械师、管理工厂的工程师等全新职业。
打字机的出现淘汰了缮写员,使得我们的手写能力下降,但它催生了打字员,并最终普及了全民性的键盘输入技能。
学习如何有效使用人工智能工具,本身就是一项新兴且至关重要的技能,它要求我们每一个使用者具备提问(prompting)、批判性评估、信息整合以及与AI协作的能力。
2、技能门槛的降低与知识的普及:
许多技术在“替代”高门槛技能的同时,也极大地普及了知识和创造能力。
印刷术使书籍不再是僧侣和贵族的专利,普通人也获得了阅读和学习的机会,这无疑极大地提升了整个社会的平均知识水平。
同样,数码相机和智能手机的摄影功能,让曾经需要高深光学知识和暗房技术的摄影艺术,变成了普罗大众记录日常和表达生活的方式。
AI工具,如代码生成器或数据分析平台,也可能降低特定领域的入门门槛,使更多人能够参与到过去只有少数专家才能从事的创新活动中。
3、技术升级过程中的认知焦点的转移:
技术的介入往往将人类从繁琐、重复的低阶认知劳动中解放出来,从而可以将认知资源聚焦于更高层次的活动,如战略规划、创造性构想和复杂问题解决。
计算器的普及让我们不再需要耗费大量精力进行繁复的四则运算,转而可以思考数学模型背后的逻辑与意义。
AI的出现,理论上也能将我们从信息搜集、初步草拟等任务中解放出来,专注于思想的深度、论证的严谨性和创意的独特性。
因此,历史表明,技术进步与人类技能的关系并非简单的“你增我减”的零和博弈。
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,其中,旧技能被新技能替代,高门槛技能被普及化工具赋能,认知焦点也随之向更高层次转移。
真正的风险不在于“失去”某些旧技能,而在于我们是否成功地培养出了驾驭新技术所需的新技能,
以及是否保留了那些支撑高阶思维的底层核心能力。
案例:新加坡的技能创前程计划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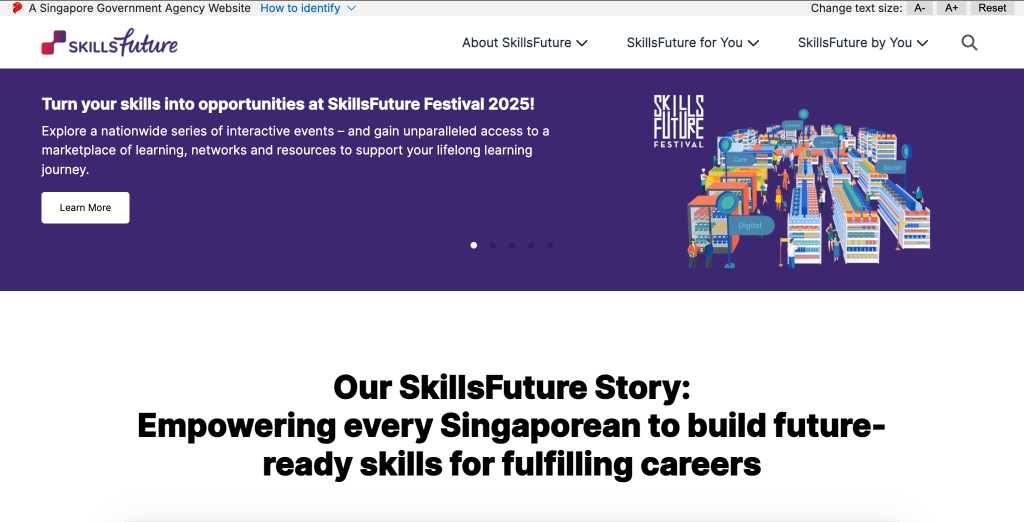
https://www.skillsfuture.gov.sg
| 新加坡政府将“技能创前程”计划定位为国家人力资源开发核心战略。 2015年,新加坡政府启动“技能创前程”计划,将原先的劳动力发展局重组为技能创前程局和劳动力发展局,分别专注于技能培训和就业。技能创前程局采用“个人技能账户”制度,为25岁及以上的新加坡人提供每人500新元的技能培训津贴。 2024年5月起,新加坡政府又通过“技能创前程进阶计划”,向40岁及以上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新加坡人额外提供4000新元的培训津贴,以支持其获得实质性的技能再培训和能力提升。培训课程覆盖数据分析、智能制造、网络安全等新兴领域,共计7000门课程。这种“个人主导、政府支持”的模式,使劳动者技能提升从“被动安排”转变为“主动规划”。 |
英国学者Stephen Wood在其1982年编辑的著作《工作的退化?技能、去技能化与劳动过程》(The Degradation of Work? Skill, Deskilling and the Labour Process)以及1987年发表于《Acta Sociologica》的论文《去技能化辩论、新技术与工作组织》(The Deskilling Debate, New Technology, and Work Organisation)中,对“去技能化”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与反思。
Wood认为,将技术与去技能化直接挂钩的观点过于简化,他强调了技术的非中立性(其应用受管理策略驱动)、工作组织的复杂性以及工人所拥有的“默示技能”(implicit qualifications)的重要性 。他指出,去技能化并非一个必然结果,而是受到管理策略、工人抵抗等多种社会因素调节的复杂过程 。
到了20世纪90年代,随着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的兴起,一种截然不同的理论逐渐占据主导地位,即“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”(SBTC)。
该理论认为,技术进步并非普遍地降低技能要求,而是偏向于与高技能劳动力互补,同时替代低技能劳动力。
进入21世纪,研究者们发现SBTC理论也无法完全解释所有的劳动力市场现象,例如中等技能、从事常规性任务(routine tasks)的岗位(如文员、流水线工人)大量流失,而非常规的手工任务(如护工)和非常规的认知任务(如管理、研发)则持续增长。
这就催生了“任务偏向型技术变革”(Routine-Biased Technical Change, RBTC)理论。
该理论认为,技术(尤其是计算机和自动化)主要替代的是那些可以被编码和程序化的“常规性任务”,而对需要情景适应、人际互动和创造力的“非常规任务”则起到互补作用。
如今,人工智能的崛起为技术与技能演变这场辩论注入了新的、更复杂的变量。
早期的自动化主要影响体力劳动和常规性认知劳动,但生成式AI正开始涉足过去被认为是人类专属的“非常规认知任务” ,如写作、艺术创作、战略分析等。
技术对技能的影响是一个从“普遍降级”到“结构性偏向”,再到如今“全面渗透”的复杂过程。
在“普遍降级”阶段,技术的出现使得许多传统技能变得不再必要。
进入“结构性偏向”阶段后,技术开始对不同技能产生不均衡的影响。高技能者往往能够通过掌握新技术获得更高的收入和职业发展机会,而低技能者则可能被边缘化。
然而,随着AI技术的进一步发展,我们进入了“全面渗透”阶段。
AI不再局限于执行简单的任务,而是开始介入需要高度认知能力的工作,如数据分析、决策制定、创意生成等。这使得AI不仅取代了传统意义上的“体力劳动”,还开始挑战那些被认为是由人类独有的“高阶认知能力”。
AI时代的根本性挑战在于,它潜在地威胁到了过去被认为是技术无法替代的、位于技能金字塔顶端的高阶认知能力。
本文成文得益于秘塔AI之深度研究辅助,
其中不少文字源自其所生成的深度研究报告。
特别鸣谢!

Photo by Johnnie Walker